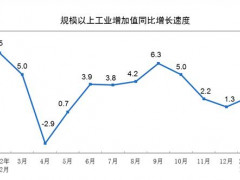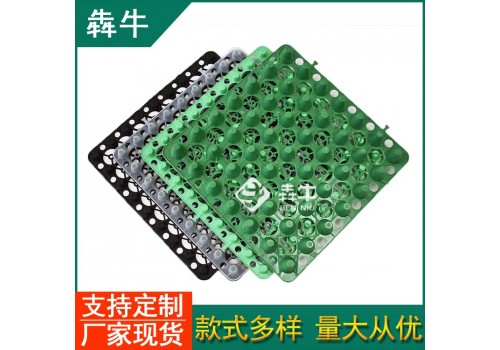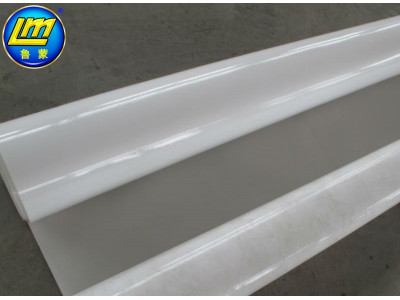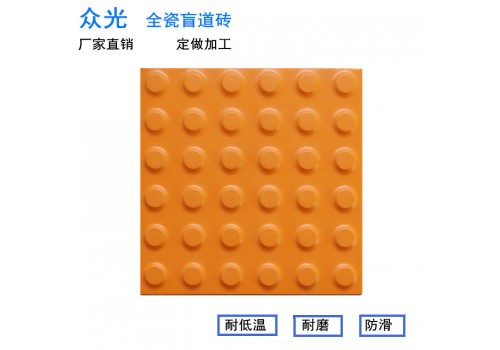从大学走向社会的过程里,无论干什么都有那么多的选项,yes or no,A B 还是 C,把每一个自我淹没在无边无际的考量和不安里。那些选择的重量会让你怀疑,按下选择的这只手能承受它带来的后果吗?是不是应该保持默认,接受父母建议,过上别人帮你规划的生活,才会过上更轻松一点的日子?但那样的话,你自己又在哪里?
从大学走向社会的过程里,无论干什么都有那么多的选项,yes or no,A B 还是 C,把每一个自我淹没在无边无际的考量和不安里。那些选择的重量会让你怀疑,按下选择的这只手能承受它带来的后果吗?是不是应该保持默认,接受父母建议,过上别人帮你规划的生活,才会过上更轻松一点的日子?但那样的话,你自己又在哪里?“选择到底意味着什么?为什么你要一直选来选去的?为什么要在不同的鞋,不同的衣服,不同的家具,不同的住处,不同的生活方式里选择,选择,选择?为什么你闭眼点击下一步,为什么不轻松地接受命运安排给你的默认选项?你每一步去精挑细选就是对的吗?你又怎么知道?”
我们和 “自如海燕计划” 想一起帮你找到你自己的回答。我们走出办公室,寻访了一批在18岁到24岁的人生转折期里面临选择的年轻人,他们也许就是你身边的同学或对桌新来的同事,他们的忧虑与困惑一点也不比你少,但他们都在无数可能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姿态与方式 —— 希望你也能。
高言是在大四发现自己再也不喜欢 b-box 了的。
六七年前,他在初中期间喜欢上了 b-box,那么时候身边没人可以一起玩,他就在网上找伙伴,在贴吧,在优酷的评论区跟人交流。大学到了上海,为了聚集起有这个爱好的人,他还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 b-box 社团。
一直以来,“b-boxer” 都是他重要的认同感来源。他会这么跟人介绍自己,也愿意在众人的邀请下来一段,但现在他不愿意了。有一天,他去参加了几个上海 b-boxer 的聚会,在那个聚会上,他忽然感到一阵不适,过去熟悉的场景突然变得陌生。
“我觉得他们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没劲。”
从聚会回来之后,他把微信头像换成了天线宝宝里的 “诺诺吸尘器”,像是要躲回到一个更安全和简单的世界里。

被挫败的期待:我是谁?我在这干什么呢?
扎西是高言在这所财经院校里的同班同学,他是藏族,来自拉萨,但高中就到了上海读内地班。他普通话说得很好,甚至还会带一点江浙口音。高言忙着张罗社团和踢足球的时候,扎西觉得,他根本就是来错了地方。
还没上大学时,扎西看过一部吉卜力工作室的电影《来自虞美人之坡》,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初,从战后复苏中的日本,旧的事物被摒弃,人们谈论着新鲜的一切。在他的想象中,那是大学应该有的样子:“宿舍特别旧,但大家有很多社团,很多样,虽然你研究哲学,我研究化学,但我们能特别放松地互相交流。”
可是财大的氛围很保守,完全挫败了扎西的期待,草坪上没有高谈阔论的学生,只有说着上海话遛娃的小区居民,学生们行色匆匆,不是在看手机,就是在回寝室给手机充电的路上。

大一时,他有一阵子每天都睡不着觉,感觉自己像头困兽,被束在宿舍里那张窄窄的床上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这里,不知身边的人和自己有什么共同点,最重要的是,不知道要怎么逃离。
好在大二快结束时,遇到了喜欢音乐的朋友,看到别人自己做歌,他想,“Why not?”从此也开始学着做 beats,用藏语和汉语写词。对于一个敏感的人,只有创作才能够让他感到最大的解放。

未来的选择:失序的世界里,我想先要点安全感
比起扎西的不适,高言更快地接受了被暗示的规则:“进了这所学校,其实未来的出路比较清晰了,大家都去 ‘四大’、银行、证券。”
财经院校的氛围自然要实用些,大家进校就开始考证,从 CPA 到 ACCA,哪怕他们在人文学院,证也是能考全都考,毕竟 “来都来了”。
高言选修了不少财经类课程,也在考 ACCA 的证书,社会学毕业后,他打算工作一阵子再考法律类的研究生,“这样可以事法律审计的工作”。面对复杂的成人世界,跨边界的职业化是高言能想出的应对办法。
证书被炒起来也是这几年,跟身边的同学一样,他也怀疑这是不是一场大骗局,以后市场需要这么多的持证人吗?但他能确定的一点是,“能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挣钱,感觉非常好。”
高言的心里住着一个喜欢把事物装进方格的人,他向往一个秩序井然、容易理解的世界,但出去的第一场面试就把他弄蒙圈了:同一场面试的人里,从专科到博士生都有。“外面的世界好像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结构化,基本上还是无差别竞争”,所以,考一堆证书有什么用?你有了证书,你就是市场需要的人吗?

不安稳与不确定,或许是全人类的处境,而 “保障感” 则是高言使用的高频词。还有几个月离开校园时,他为自己找到了两个 offer,一个是银行,另一个是家电公司的市场营销,两份工作的稳定度不一样,但他还在衡量。衡量来衡量去,他发现自己最害怕的原来是 “回家”,去干家里帮忙安排的工作。他不怕别人怎么看,但害怕自己不再学习和成长,害怕自己在精神上迅速地老去。
学校的食堂旁,有一小片空地挨着宿舍区,也连着超市和球场,是一个简单舒适的公共区域,来自西藏老家的朋友下了课都来这里聊聊天,大四的话题自然是未来,而除了扎西之外,大家都打算毕业以后就回家了。
“十二、三岁就来内地读书了,我们总要回去的。”
“回家” 像是一个嘀嗒作响的背景音,回响在每个人的身后。只不过有的人近一点,有的远一点。“我们都离家久了,父母的身边没有人陪。” 但扎西的爸爸妈妈没有催他回家,只是他内心深处知道,一个来自西藏的孩子,或许总有一天是要回家的。
在外读书的日子像是某种现代的游牧,高原的冬天气候寒冷,回家的路也太漫长。在内地读书的这几年,扎西说小时候带自己的长大的老人很多都 “没了”,不少老人熬不过冬天就去世了,等夏天回去才发现,家里的人少了一个。
但一旦回了家,就得面对单一而保守的环境,他几乎不会有个人的空间,一个人的社会地位、权力与声望都来自于他是哪个体制内单位的人。妈妈虽然支持他写歌,但那种氛围还是让他害怕,怕自己不得不变得很 “社会”,和人抽烟喝酒,用一样的套话,一样的手势。
回去生活几近于在二十岁退休,但一直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也能令人发疯。到底什么是重要的?那些睡不着的晚上,扎西回答了自己: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失败是,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天,却想着 “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拼一拼”。
外面的世界里有太多可能性,扎西想知道他还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他决定不给自己设限,“哪怕有实际的困难,但感觉对的就尽可能去做。”
回家,等四十岁的时候再回家吧。

球场和房间:有一天自由总会有的
三年多的混战后,他们快毕业了,但高言和扎西都常常忘记,他们七月就要离开学校。
五点钟,高言说得回去接着改论文了,他的论文题目有关趣缘社群,研究因为对足球的共同喜爱而聚集在一起的团体。论文题目是他和导师一起确定的,发觉了自己对 b-box 的冷淡之后,足球成为他仅有的乐趣。
高言说,如果没有限制,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去西班牙,去巴塞罗那,“最好能找一个在球场边修草坪之类的工作”。没有竞争与对抗,没有其他人的挑战,只有热烈的阳光,散场后的球场里让人沉醉的空旷与寂静。
仲春的阳光很充足,关于未来的决定已经做好了,高言跟扎西都感到难得的放松。大学四年,好像最奢侈的竟然是这点空闲,放在生活里,像是偷来的东西。
想到未来,最让扎西激动的是可以住进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房子,像任何心怀创作梦想的年轻人一样,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,“大家都可以来,我们想怎么装饰就怎么装饰,墙上可以贴我们喜欢的画,不一定是做歌的,画画也可以,我们可以有一段友谊,大家在一起很舒服,然后可以开心地做东西。”
“现在的状况像是被束着一只手,你明白吗?” 他说,“如果可以这样的话,就可以很自在了”,说这话的时候,他往后靠在椅子上,双臂张开,做出拥有很多空间的样子。

在人类学中,人类学家用 “通过仪式”(rite of passage)来描述个人生活随年龄增长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过程。在人类文化中,长大常常是一场折磨跟试炼,通过了这场试炼,则确定你是一个可以尽到责任,享有权利的大人,这个过程,不是那么浪漫。
大学的时间被 “考证” 吞噬掉了,就业竞争的前置,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必须更深地陷入进去。就业竞争也是阶层的竞争,它从职场期向前蔓延到高考期,走出家庭,走到外部,完整对接,严丝合缝,身在其中的人要么接受,要么离开。“闲逛、游荡,不合时宜地阅读与思考” 的 “游荡者”,似乎只能存在于社会主流与个体意愿之间的缝隙中。
如果说一个刚进入大学的新生,需要的是更多的选择,那么正在面临毕业的高言和扎西,必须在种种选项中减少自己的选项。高言在思考中生长出了怀疑,他怀疑选择到底是不是都是假象,人究竟能否做决定,人能否拥有自由,“我们是否都在扮演那个角色,只是有人演得投入,有人演得勉强?”
大四的人生,就像站在一场 party 散场后的紧急出口里面,看着逐渐吞噬掉快乐的晨光降临,不过艰难和不快的选择仍然好过没有选择,不是吗?(转自:VICE)